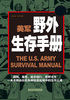
简介
精彩点评
-
ㅤ推荐
草根一路走来,野火烧不尽的,留下来,都有几分强韧,也有几分世故,不像贵族,于自制中得到自由,举手投足有底气,大可坦然地发梦,失败了也有几分可爱。--双雪涛 笔风有着村上的影子,若说是林少华写的我也信。双雪涛,好似小说中人有双人影,雪有重叠时。
-
🔥ZLMing推荐
九故事 这本作品集,九篇小说,都不算长。据说是受了塞林格《九故事》的启发而作,卒读后虽感觉少了些惊艳,但短小精悍的特点的确颇为相似,这应是作者爬罗剔抉的结果。 九个故事篇幅不长,我却读了不少时间。读完一篇,需停下来歇一歇,才能继续。我的祖籍在东北,作为双雪涛的学长在那里也生活过几年,再加上亲朋好友留在关外的不在少数,所以故事里的人和事总会不经意间使我我触景生情,难以自拔。笑传,历史书上的事,除了人物全是假的;而小说则刚好相反,除了人名都是真的。前半句不好妄加评论,后半句我是比较认同。 故事给我带来了不易消化的感受,强烈而真实。每一篇结束的时候,那种慢慢累积起来的感受迟迟不肯散去,似乎就此停留下来,在我的情绪和意识里占据了一个位置。 每篇虽然独立,却又是可以互相参证的,它们大多是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里的故事。国企改革、下岗潮等大时代背景下,人如蝼蚁般被大潮席卷、淹没,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人也多是遍体鳞伤。写的虽是小人物,但不该被符号化为“底层文学”。这些作品触须尖细,探及特定时期的历史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复杂境况。故事的讲述细致、平静、克制,文笔既显示出相当成熟的一面,又不是年轻人的朝气,可读性很强。 双雪涛是一个八零后。迄今为止创作了不少的优秀作品,我查了一下,有不少作品斩获颇丰,大大小小的奖项拿了不少。这是一种不凡的能力——把眼光从过去扫向未来,努力探寻着这一特定时期的偶然与必然,并从中发掘和领会与自我密切关联的方方面面。 看他的文字,他写的略带村上风格的故事,或许需要读者得具备些耐心。即使感受不到什么,即使在心里什么也未曾留下,只要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有趣,也是收获。
-
曹幸艺推荐
《冬天的骨头。》 标题借用双雪涛在【一席】演讲的主题,同时也是美国一部小说的名字。 严格来说,我是2017年才听说双雪涛这个名字的。当时我和朋友在广州方所听一场止庵老师的讲座,回学校路上朋友说起双雪涛,说下个月双雪涛在方所有场讲座,查了资讯后发现是青岛的方所,她一阵落寞和遗憾。 而我,那个时候便把《飞行家》收入书架,今年才终于打开它并完整读完,很惭愧。 双的小说里总是离不开灰败的烟囱、衰落的北方、铁幕般的大雪之类的景象,还有自杀的父亲、跛脚的母亲、出轨的我等等,总是充斥着奇人异事与侦探悬疑的色彩。很多笔触更让人想起村上,当然村上也是双的文学偶像,把小说家当作毕生职业的灵魂信徒。 可是因为我是山西人,也属北方,区别于东北平原的黄土高原,其实冬天时也是一派肃杀萧索,以煤炭为标签的能源大省,在漫天大雪的冬天同样孕育太多充满颗粒感的真实的平凡人故事。在看到双雪涛小说中对沈阳冬天的很多很多描写时,总是眼眶一热,好似看到了童年时的光景。 我喜欢他在平实朴素的文字中藏着的千钧力量,喜欢那种曲折迂回的小说构思,看《光明堂》有时会想起《解忧杂货店》。很多时候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看着看着就会出神,陷入沉思无法自拔。 我牵着姑鸟儿往家走,想着下上三碗面,每碗都有鸡蛋和葱花; 李明奇的热气球最后升上了夜空,虽然不知去往哪里; 小说家挽着年迈的母亲,一齐跛着消失在黑暗里; 或许,我会不顾一切地将海豚放回大海里; …… 太多太多地方了。双的小说实在是需要多看几次,多咀嚼,真的会咋摸出不同的味道。 双雪涛曾在台北一家二手书店门口偶然瞥见哲学家殷海光说过的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没有饿死,已算万幸。 27岁前,他从未想过走上写作这条路。《翅鬼》一出,命途转折,他成了那家国有大银行20多年来的第一个裸辞者。 他曾对当时的同事说:人这一生注定是尘归尘、土归土的,但是唯有文字,唯有踏实的创作这个东西可以一直存续下去,相当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所以我想把这件事全心全意地做好。 他想吃写作这碗饭,赴汤蹈火,誓要写出牛逼的小说,还有,尽量不要饿死。 我总觉得这么坚毅这么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营生会很艰难。以艺术为生,残酷得很,与浪漫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浪漫说信仰说情怀的,那都是吃饱了的人。 好在他天赋异禀,甚至被业界称为“迟来的大师”。 双雪涛喜欢记录那些故乡凡人的故事,用他的话说,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悲喜,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但是就是这些故事,对他来说意义深远得多。 他说人生可能就这么一个口袋,只能装这么多东西,一个人走来走去,身边的人一定会更迭。这种更迭是不能避免的事情,不然人生就太臃肿了。拖着好几火车皮的东西,是没办法走远路的。但有时候人心里应该坚持一些东西,在善良与诚实之外,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 这是所谓的冬天的骨头。 看过《飞行家》后,我老有一股冲动,想写小说,把记忆里的小时候的事,用文字保留下来。离开山西5年了,而且以后还会更久,每年只是春节回去一趟。我怕以后春节都不回去了。 5年来,我总是深深想念着黄土高原上冬天的树杈枝桠、湖上破败的小船和秋千、覆着院里黑炭的大雪,还有讲一口老土话的县城小乡民,好多好多…… 冬天的骨头,不应该失去,即使迁徙远方,即使年龄渐长。 2019/10/25
-
驭风牧云推荐
《迟来的大师》 ——我读双雪涛 前些日子看过双雪涛的《飞行家》,一直心有余悸,念想着这是哪里横空出世的一尊神!这两天追看了他的《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重看了《跷跷板》《光明堂》,又找来当代文学大咖们和各种文学平台对他的推介,顿悟了一个道理:有些人天生下来就是小说家,有些人埋头苦耕一辈子顶多也就是个文字工作者。 1.迟来的大师 名家成名之前要经历多少投稿石沉大海的煎熬,遭受多少退稿弃稿改稿的折磨,然而这个姓举世无“双”的双的83年的天才作家,用手指肚轻轻一叩便捅破了文学这张窗户纸,他十几天写就的《翅鬼》投给台湾举办的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便毫不含糊的把60万新台币收入囊中。当时都忘了参赛这个茬的青年双,过了多少天后,在朋友的再三催促下,才慢吞吞的发个邮件咨询情况,十多分钟后就收到了回信:终于找到你了!因为他投稿时没留任何联系方式,只有大咧咧三个字——双雪涛!评奖委员会满拉世界寻摸,也想不到这位初出茅庐的小爷,隐藏在沈阳铁西区艳粉街的影子里!随后的《平原上摩西》《聋哑时代》《飞行家》《天吾手记》陆续出版,一下子在两岸文学界炸开了锅,三十出头的双雪涛,懵懵懂懂的被扣上了镶着“迟来的大师”“遗落的大师”金边的帽子! 想起许知远对马东的访谈:引领时代巨轮前进方向的是百分之五的人类精英,百分之九十五的都是追随者……双雪涛一定是这百分之五里的!想起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里一段话:在一个民族中,总要有上百万人的存在,一位天才人物才能从中走出……双雪涛一定是百万分里的之一。 2.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双雪涛成长在沈阳铁西区的艳粉街,也是他小说里出现最多的地名,据传是当年给皇家种植胭脂的地方,名字听着很香艳,却是东北工业没落凋败的见证地!那里是棚户区,居住着大量的下岗工人,无业游民,隐藏的罪犯,赌棍酒鬼和妓女,滋生着迷茫麻木阴暗绝望和犯罪。双雪涛父母下岗的时候,父辈的同事们争先恐后的把工厂的零件工具器材搬回自己家时,只有他父亲扑向了厂里的图书馆,当他的伙伴们把青春和热血投向街头械斗时,他埋头啃着大部头。人在昏暗的艳粉街,心却野向了文学的殿堂! 双雪涛写的最得心应手的也是最好的《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跷跷板》《光明堂》,都设定在艳粉街!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看看那些成名的大师级作家,笔触一落在原生地,才华才真正放浪起来,照亮整个世界。马尔克斯生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所以才有《百年孤独》;陈忠实出生在陕西原上,所以才有《白鹿原》;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所以才有《红高粱》《蛙》;阿来出生在四川西北藏区的小山寨,所以才有《尘埃落定》;阎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小村庄,所以才有了《日光流年》《丁庄梦》……那些离开母体离开原生地,貌似胸怀整个世界,实则虚无缥缈,又没有大量史料基础和文学基因的作品,一定是矫揉造作惨不忍睹的,或许高光一时,很快便烂在臭水沟里! 3.野兽长大之前也是乖巧的 读双雪涛的小说,开始摸不着头脑,东一下西一下,叙述着杂乱无章的事,就像在摆俄罗斯方块或者在布一场象棋围棋局,每一步你都看不出他想干什么,左一个子右一个子胡乱摆着,也不进攻你,你也进攻不了他。等到你看出苗头,找出棋子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时候,你已经死在他的笔下了。阅读的成就感和挫败感像海啸一样壁立而来,成就感来自于你终于看懂了他的棋局,挫败感来自于我操真牛逼,这货是怎么布局的,在他面前溃不成军,真想给他跪下,叩拜不杀之恩! 他用笔从来不炫耀不废话,不搔首弄姿,不斟词酌句,不风花雪月,不哀怨忧郁,几乎极少写风景写心理写艰涩的话,下笔冷峻,笔锋阴森,基本全靠人物对话铺排故事的发展,车轮般一直往下走。可是就在这平铺直叙朴实直白的话里,不停步琢磨不打紧,一停下思考,就让人心惊肉跳:废弃的工厂里幼儿园跷跷板下面埋着一个死人,而这个死的人还活着;海豚看着挺高兴,可实际上你把他的脑袋剁下来,它的嘴型也还是那样,惊悚的描述;送给心爱女生的贺卡,专门选了带凸版的,她黑夜里用手指就能摸出是什么东西……这些惊悚融进他的叙述里,看似漫不经心随心所欲,可是越往后看,越感受到他的野心,当野兽长大那一天,给你心灵恶狠狠的一口,半天回不过来神来! 4.苦难是文学的催情药 改革开放四十年,风起云涌!但从经济上讲,是属于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样地域的四十年,不属于东三省,或者说至少二十年不属于,特别是最近的二十年。相比较于京沪广深杭的蓬勃,东北的不振不举更具凋败的气色。上海云集各路金融大鳄,深圳广东云集华为格力、保利恒大这样的制造和地产大鳄,杭州只有马云一条大鳄就够了。再看东三省,感觉印象深刻的是大批下岗工人和他们钟爱过的蚁力神、中华憋精,满大街的无限极、权健养生馆,足疗店洗浴中心,还有近些年火速崛起的网络直播。 近期看到两组数字挺有意思,一组是汽车销售大幅下滑的数字,高居榜首的是东三省,降幅高达百分之三十三,东北人买不起车了,实打实的消费降级,想想十六七年前纯进口悍马霸道基本都被东北人和山西人买走了,一个进口车展销会的豪车竟被一辽宁人包了,今非昔比令人唏嘘!另一组数字来自于现在被全国人口诛笔伐的天津权健集团,权健火疗馆全国开的最多的第一是黑龙江,第二是辽宁,而且远远高于其他地域,我们都知道的是,权健庞大的资产体量下涌动着的是欺骗贪念和嗜血疯癫,无数中老年人的毕生积蓄也满足不了权健贪婪的兽腹。 说这么多和双雪涛无关的话,其实想说的是近二十年东北人口流失、人才流失、技术流失、资源流失的背后,造就了更多的底层人和边缘人,那种传统重工业模式迅速崩塌后产生的迷茫和挣扎,滋生了苦难的沃土,而双雪涛正是成长在这种环境下,用他敏锐的眼光观察身边苦难里的阴暗和罪恶,吸收它记忆它思考它咀嚼它,然后长大成为文学,便极具冲撞力。 苦难产生的不仅仅是罪与罚,是悲剧性的底色和喜剧性的旁白,而且还会造就一批思考者和文学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榜单,很好的佐证了这一点,几个有影响力的文学平台——“鲤”“腾讯大家”和“理想国”在今年搞了个匿名文学奖计划,相当于歌坛的蒙面唱将猜猜猜,一些名家和新手在匿名状态下把作品呈现出来一较高下,最终十个作品入围大名单。有意思的是双雪涛也在其列,其中除了马伯庸、笛安等名家入围,最大牌的是目前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人选阎连科也在其中,但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无名小辈郑执的《仙踪》,我看过后极具震撼力当之无愧,和双雪涛的底色有点像,原来他也是沈阳人。同时入围的还有另外一个沈阳人,班宇的《海雾》,也就是说包括双雪涛在内,前十名里有三位东北沈阳人,占比百分之三十三,和前面汽车销售量下滑的比例一模一样,真有趣!换句话说,在南方和东部经济蓬勃井喷产生越来越多的财富大鳄的同时,经济凋败没落的东北正在长成一个个文学大鳄!苦难造就悲喜剧,悲喜剧催生文学,这句话太有即视感了! 也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几天被双雪涛小说强劲的冲撞力下,还能活着写了这么多!
-
昨日宝物🍒推荐
《飞行家》共收录了双雪涛的九篇短篇小说。缘起——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下虚构的记录;沉淀——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张力编织进故事的纹理里;扎根——让爱、梦想、尊严和自由在卑微和绝境里重生。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是没落的北方城市。艳粉街、影子湖、光明堂、红旗广场、春风歌舞厅、红星台球社……这里布满破败的街道、废弃的工厂,流窜着形形色色的人。故事里的角色大多是被遗忘的边缘群体。久藏、小橘子、疯子廖澄湖、“少年犯”柳丁、姑鸟儿、驯养师阮灵、“疯马”马峰、“飞行家”李明奇……他们是被历史的大潮拍在岸边的鱼。在《飞行家》里,就是由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些地方,让凡人的热血、尊严和自由绽放出火光。 这是本书的简介,也是我看过最实在最贴切的简介。没有为了阅读量而吊人胃口,没有为了引人点开而名不副实。而它的简介也如同本书及其作者一样,质朴纯粹。它单独成章,它就是一篇最短小精悍的书评。 接触本书的契机就是因为《刺杀小说家》电影的上映,微读也在大力推荐本书。应该是从众心理吧,在此驱使下,我点开了本书。第一篇《跷跷板》说实话,让人不知所云,云里雾里,不知道为什么死者活着却真的有具尸体。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这本书的评分如此低。在耐着性子继续往后读时,我发现作者是个极具思想的人,小说本是虚构,而虚构里的故事还有隐喻,是评判,是讽刺,是呼唤,是觉醒。小说的立意深远且引人深思。我这时才明白,此书是一枚沧海遗珠。它的文学价值与它的评分严重不符。快餐时代的人是否只适合读一些轻松的文章? 九篇短文,三个时代,一类人的人生。 书中的故事都聚焦于小人物,讲述他们平凡却又起伏的人生。但无论命运多么坎坷,生活多么不如意,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思索并向往美好。正如同本书封面写的那样“大雪覆盖不了凡人的热血,尊严和自由在绝境里逢生”。渴望美好是人之本能,但置身社会这个巨大的熔炉里,还有多少人能够独立思索呢?整本书给我一种飘忽的深沉感和轻松的疼痛感。作者总能把握好痛苦与绝望、积极与颓丧的度,发人深省却不至于沦陷。我想,这就是小说存在的意义吧! 正如作者所言: “一颗高贵的灵魂,总会超越于现实之外,于精神的世界里去寻求一种更高贵的存在。” “我用自己笨拙的大脑创造一点点东西,印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实体,遥远的某个人,关上门倚在床上,拿起她,用他(她)的灵魂去识读,是我能够对抗这孤独的唯一方式。重要的并不是谁创造了这个东西,重要的是你摸到了她,闻到了她,认出了她,然后认出了自己,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哪怕只有一瞬,我也感到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