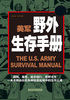
简介
精彩点评
-
科科科科推荐
挺有意思的写作风格,有些不知所云的叨叨,意外的让人能看下去。小说家真的不适合拍成电影。
-
信天游推荐
结尾大部分都没给出交代,把人抓在半空吊起来不知所措:这就完了?!天马行空的走笔,读进去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
ice bear推荐
喜欢北方和宽吻两篇。 小说的东北特点非常浓郁,不是说语言,其实语言反倒不是很东北,比如我从来没见哪个东北人跟家里长辈说话还用您字的哈哈😄我觉得这个东北特点体现在人物的行为方式,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有天差地别的处理方式,但是书里面写到的这些行为,放在东北的背景下都让我觉得非常合理,甚至换一个城市你都觉得不行,这里的人不是这样做事的。一个地方的人的共同点,绝对不只是体现方言或者性格这么表面的东西(其实性格也根本不十分具有地域性),反而是体现在行为方式上更多也更统一。
-
Leslie推荐
还不错的短篇集,语言风格在已知的中国作家里算是很少见的,平铺直叙的魔幻现实主义,很多比喻都妙到极致。
-
LITTLE GHOST推荐
可能我读的书还少 类型更少 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文字 这样的作品以及这样的作家 我读这本书很迷幻的感觉 里面的字都认识。可连在一起我就常常不懂作者想讲什么 我感觉书里内容跳跃性很大 我会回头再读一遍的 也许是几个月后 也许几年
-
嘻嘻推荐
短促有力,终点不远。 好久没看双的书了。记得去年初见时候的惊艳,再到后来些许腻了,今又再捡起,再次感叹双的才华。 是那种我能触摸感受到的真实,我是说文字,和人。全都像真实存在着的,跃动着的,冰冷的,热烈的。 唯一让人有些怅然若失的就是每篇短篇的结尾,好像总觉得该有个更好的结尾,更好的,更容易刺穿我的。虽然已经被扎的千疮百孔了。 就像冷箭一样,在你多悠悠的时候给你一下,疼的不行。 另:刺杀小说家不错,但有更多更好的双的作品更该被搬上银幕,或者一篇也不要拍。
-
此间推荐
在我的观念里,包含着黑吉辽的东北和包含着山西河北的华北(山西有的地方也不在华北)是一样的地方,在共和国成长的几十年间,这些地方以及这些地方的人们经历着相似的生活,黑吉辽河北轰隆隆的重工业,山西黑黢黢的媒,都为共和国架着骨头,输着血。因此,作为一个山西人,我对双的好几篇小说还是很有共鸣,很有感触。敬时光,敬平凡,敬淹没在时光中的平凡的人和事。
-
万一推荐
这是一本不知道该怎么推荐的书,但还是建议你们读一读——值得一读。
-
神经蛙推荐
觉得和张悦然风格有相似的地方,可能很多80后作家多少都受点村上的影响。而他们的十几岁刚好赶上《萌芽》(为什么输入法首先出现“萌娃”)、新概念的鼎盛时期,“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理念在被束缚了许久的大众文学中脱颖而出,经过这样一群渴望宣泄敢于创新的青少年的摆渡而不断壮大。 作品中象征的表达实在太多,直觉的脑回路凿浅了,理解不到位或根本就理解不了,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也是相当了得,几乎没有一篇小说是常见结构的,不过适应了也就O了。越挖水越深,越嚼越有味,绝对不会吃完甘蔗满嘴渣,或如口香糖,咽进去的都是唾沫。 全书不见常规对话,不见问号、引号、感叹号,但一点也不耽误它的完整。都说,人长得靓不靓帅不帅,头发剃光了看看(鹿晗在“上海堡垒”里的盖住半个脑袋的“军人”造型活该电影扑街,杠粉闭嘴),小说一样,零零碎碎的东西加多了反而看不见皮肉摸不到骨头了。 最后,被一书友震撼到了,全程的点评和解析精准的不像话,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令人望尘莫及。总有被剧透的气结和被抢答的懊恼,也是服了,认了~感谢。
-
皮吖推荐
初读双雪涛的书,透过几则故事,他以一种舒缓、甚至是轻快的反讽语调叙述着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对于东北工业区的历史,好似偶尔会暼向几眼,而后投入几个漫不经心的眼神,然后再继续心无旁骛地讲述他的故事。事实上,当我意识到历史贯穿在他的故事中的时候,我才发现,双雪涛早已把历史与人、社会之间的对峙和矛盾过程编织进了故事的纹理中。
-
清欢推荐
这本书虽然名叫《飞行家》,但却是双雪涛老师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全书共9篇,《飞行家》只是其中一篇而已。 双雪涛老师,并非是名震四海,但正是这一位83年的作家,却以其十几天写的《翅鬼》斩获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之后的《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飞行家》等作品,更使他的名字印在了两岸文学届直间。并为他带上了“迟来的大师”,“遗落的大师”的称号。双雪涛老师,无疑是一位天生的小说家。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便是双雪涛老师对东北老工业区的怀念以及对下岗工人的一种致敬。双雪涛老师身为一位东北小说家,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了钳工,铁西区的艳粉街,红星俱乐部,红旗广场,烟囱等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名词。《飞行家》中的烟囱,《刺杀小说家》的烟囱,对于作者来说,这可能就是一种对于童年的回忆。在如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信息革命、科技革命的时代,烟囱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的符号。正如《飞行家》中“我”对大姑要拆烟囱而表现出的态度一样,烟囱不能拆。因为烟囱还在,那至少代表着这一段历史还存在过。 在作者的眼中,工人是要致敬的,但是正是这一批批的工人,却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了渐渐被人们遗忘的下岗人群。在双雪涛老师的作品中存在多次隐喻,有时这些隐喻或许不是不说,而是因某种原因而不能明说。《跷跷板》中在“我叔”刘庆革病重的时候,一直在通过“我叔”之口,叙述着一起杀人案。尽管埋在跷跷板之下的那具尸体或许并非是甘沛元,但他也会是其它的一名被约谈买断的下岗工人。记得在另一部小说《奋斗者,侯沧海商路笔记》中看到的,下岗后的工人,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光,甚至连温饱也成为了基本问题。而对比之下,“我叔”刘庆革则是改革的获利人。改革前是工厂厂长,改革后合伙做企业。名字庆革,也有着庆祝革命之意。但那具尸体的主人,则要永远被人遗忘。“名字也许没有,话总该写上几句。”这是我挖出尸体后蹲在旁边所想着。没有名字,这不正是意味着工人们正在被历史所淘汰吗? 作者出生于80年代初,时值改革开放热潮。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蕴含的脱离集体,富有独立,自主,自由开放的思想也体现在小说之中。《光明堂》中姑姑独自一人前往南方寻找杀人凶手为林牧师报仇;《飞行家》中李明奇对飞行梦的追求,坐着自己做的热气球飞向理想的地方;《刺杀小说家》中去看北极熊的父亲以及执着于写小说的小说家……他们这些人无一不是为自己的理想而活,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逃离时代的束缚。 在我看来,双雪涛老师的作品也许很多还不够成熟,但其言语犀利,短小精悍;内容虽为东北,但却反应整个时代背景;结尾往往戛然而止,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让人们回味无穷。
-
小青蛙推荐
我喜欢《宽吻》>《间距》>《飞行家》 小人物炮灰似的经历没人会在意,我可以隔着屏幕说爱章宇,喜欢无名之辈他扮演的憨贼,喜欢风平浪静里的他,喜欢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可是现实里的小镇边缘青年,你怎么爱呢?现实真是太魔幻了。 我们都在经历我们的经历,loser又怎么样呢?找不到同盟军,孤独终老也无所谓。书真的是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吗?不是,你读书的心才是。
-
调皮王子推荐
不知为何新版微读变成非打星制了。很喜欢双的文字,所以愿意继续读下去。
-
不会起昵称的小傻瓜推荐
没落的北方城市作背景,废弃的工厂、破败的一街道,现实的写照却给故事的讲述增添了悲凉的味道,沧桑而无奈。那些游走在社会的边缘人,叛逆倔强的少年、特立独行的“飞行家”、执着梦想的“小说家”、在罪恶与善良中寻求救赎的“传道士”们,在双雪涛的笔下,讲述着底层的生活,也彰显着生命的光与热。
-
征途推荐
看似简单平常,却蕴含着对人性的思考,对社会的沉思,几个似乎就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却能让人回到那个地方 ,面对当下的困惑! 活着的意义?理想?爱情?肆意挥洒?
